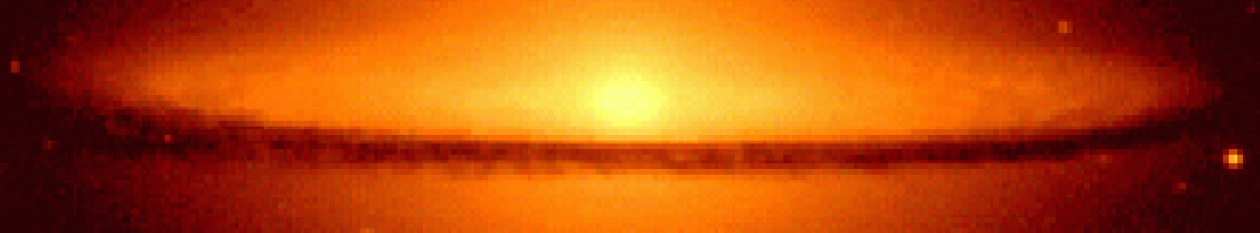作者:王令隽
万振文先生给我送来一篇何祚庥院士反对建大型加速器的意见,是登在《新语丝》上的文章。我读后有些激动。我的第一感觉是,中国理论物理学界的局面不像我担心的那样悲观,不是万马齐喑,而是有思想者,有明白人,有敢于执言的担当者。这真是中国学术界的希望和福音。
作为中国层子模型的发明者之一,中国高能物理学的理论前辈,何祚庥院士明确地表示反对在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对理论和实验高能物理学界的影响非同凡响。此事和前不久杨振宁先生明确反对在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的报道相隔不久,互相呼应,必将引起中国粒子物理学界的轩然大波和不可避免的激烈争论。
相比起来,杨振宁先生的资历和国际知名度都比何祚庥先生要高,应该是何祚庥先生的前辈。但是何祚庥先生的明确表态,其重要性决不在杨振宁先生的表态之下。因为其一,何祚庥先生的文章陈述了一些杨振宁先生没有提到的为什么不要建大型对撞机的理由;其二,何祚庥先生是中国高能物理学界的前辈和导师,许多高能物理学界的理论和实验方面的中坚,或者曾经是研究层子模型时的同事,或者是他的学生;何先生的意见将牵动整个中国理论物理学界;其三,何祚庥先生举出了一个实验高能物理学界的权威丁肇中先生来支持他的反对意见。
王贻芳和邱成桐以实验高能物理的权威自居,蔑视并嘲笑反对者为不懂高能物理的外行。丁肇中是王贻芳的老师,应该不是外行吧?丁肇中先生在实验高能物理方面的道行应该不在王贻芳和邱成桐之下吧?幸好丁肇中先生也反对建造大型对撞机。如果他不反对呢?或者在反对者里面找不到一个有点名望的实验高能物理学家,是不是王贻芳和邱成桐就很雄辩呢?是不是就可以听凭高能所的小圈子决定建造大型对撞机是否上马呢?绝对不可以!
理由之一当然是因为这种大项目耗资至巨,势必挤压其他项目,所以必须经过各方认真论证。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是:从弱电统一以后所有验证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大型实验项目,都是严格按照理论物理学家的指导来进行的。这种指导包括:1)决定实验目标,即寻找什么粒子?2)在哪个能量区域内寻找?3)用什么粒子束和什么靶?4)碰撞过程中有哪些可能的反映过程?5)所选择的反映过程必须遵守哪些选择定则(据此设计符合电路)?6)所寻找的粒子的理论能量(质量)是什么?7)对实验结果的最后认定及其对理论发展的意义的评估。
在这些重大的关键问题上,都是理论家说了算。实验高能物理学家只是在加速器设计,检测设备的设计安装调试,数据记录及统计处理等方面设法实现理论家的设想,当然也包括各方奔走搞钱。不太准确甚至不太礼貌地说,至迟在1980年代以后的高能物理实验中,实验物理学家只是为理论物理学家们打工,完全不可能脱离理论家独立地进行实验,不可能领着理论走。实验高能物理学家只是跟着理论家的指挥棒转。如果实验物理学家的结果和理论预言不符,就将被宣布为失败。
比如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花了大约十年寻找上帝粒子而没有找到,美国费米实验室也花了大约十年时间寻找上帝粒子,也没有找到。他们的实验都被理论家们宣布为失败的结果。前年 LHC 宣布找到了疑似上帝粒子(实验组自己并没有绝对把握),立即被认定为成功,宣布找到了上帝粒子,授予诺贝尔奖。由此可见理论物理学家们在高能物理实验的命运中的决定作用。所以,王贻芳和邱成桐把理论物理学家们排除在大型对撞机的论证之外毫无道理。
在王贻芳和邱成桐摆资格排斥物理学界的意见时,何祚庥搬出了丁肇中和杨振宁,但是并没有拿自己在高能物理方面的资格和学问和他们相比,是学者本能的谦虚。其实何祚庥院士自己就是高能物理方面的前辈,导师和学术带头人,资历比王贻芳高出两代。何祚庥先生对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创建作出了积极贡献。他早在1956年就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从事核物理研究,后来参与氢弹的理论研究,在氢弹材料及相应的爆炸机理、平衡和不平衡状态下氢弹应满足的流体力学方程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60年代参与“层子模型”的研究,1982年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及多种奖励,此时王贻芳还在南京大学物理系念本科。何祚庥先生曾任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1979年我进高能所和理论物理研究所读研究生时,何先生是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因为他不是我的导师,所以我一直没见着他。直到1979年底理论物理所派我出国留学时,何所长才找我谈了一次话,慰诲勤勤,叮嘱我不要忘记祖国。
何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严肃的长者,学者。我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师。出国以后,我一直没有和何先生通讯联系。2014年3月24日,我通过email 给何先生写了一封信:何祚庥老师您好!好多年没有给您写信请安,于情于义都不可原谅。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理论物理的前途和中国在新世纪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问题,有些体会,也有些建议,觉得现在是中国赶超西方的百年难逢的历史机遇,想请老师指教。因为信比较长,所以我做成一个word文件附上。望老师拨冗教正。祝老师身体康健,百事如意。学生 王令隽 叩
不久我收到李静(大概是何先生的秘书或助手)的回信,说是已转何先生。可是一直没有收到何先生的回信。我想原因大概是我的观点太极端太彻底,完全否定整个20世纪的理论物理,无法接受。后来,我把给何先生的信在人称上稍作修改,作为《致中国物理学界建议书》在我的博客上发表,被多家网站转载。何先生是否部分地接受我的建议,也不得而知。最近读到何先生反对建造大型对撞机的文章,让我喜出望外。他和杨振宁先生的意见将被证明对中国的粒子物理学界具有里程碑性的作用。何祚庥先生的文章里还谈到了一些值得人们重视的其他相关问题:
1) 大沙漠理论问题。
何祚庥先生说:“为什么美国国会质询了多位专家的意见,并在国会大辩论后最后否决了SSC项目?在学术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在粒子物理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即粒子物理再向超高能物理发展,不会再有新的发现,这被称为高能物理的‘大沙漠’ 理论。‘大沙漠’理论认为,至少要将能量提高到普朗克尺度,亦即相当于10^16 TeV的能量(王按:可能是因为网络出版的问题,原文错讹成1016 TeV),高能物理才有可能有新的发现。后来,一些高能物理学者认为这一理论并不完全正确,应有所修正。修正的办法就是引入‘超对称’的概念,并认为有了这些超对称粒子后,其能标将降低很多量级,但仍较SPPC所提出的量级高出很多很多!后来,在美国和欧洲等若干加速器均尝试发现这些超对称粒子,结果却一无所获。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大沙漠’理论的合理性。”
大沙漠理论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它不仅仅关系到中国是否需要建大型加速器的问题,更是关系到整个粒子物理学(理论和实验)的前途出路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将能量提高到普朗克尺度要求比太阳系还要大的加速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在这以下的能量范围又是理论上的“大沙漠”,不会再有新的发现。这就意味着从此以后高能物理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可做了。实验上没有新的发现,理论研究也就基本上停滞了。标准模型的理论架构非常刚性,也很难进行修正或者改善,除非将整个标准模型推倒。这倒也可能是一条路。
当然罗,仅仅推翻夸克模型是不够的,必须退到量子电动力学以前,必须退到重整化以前。大沙漠理论还告诉人们一件事,就是所谓的大统一理论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遑论什么最终的万能理论。现在的弱电统一模型都需要上帝粒子来拯救,强相互作用理论更是焦头烂额,还侈谈什么大统一理论和最终的万能理论呢?既然面临着不可逾越的大沙漠,高能物理学界其实可以做一些实事,那就是把已经收获的标准模型应用到其他科学领域中去,特别是粒子物理的近亲核物理和凝聚态物理,展示一下基础科学的威力。
如果粒子物理学界真能够将理论物理应用到这些学科,推动其发展,比什么议会的院外活动都更有说服力,也更能得到社会的支持。可是有些理论家,比如史迪夫温伯格,就坚决不承认这是粒子物理学家的责任。他说这是应用物理学家的事情。温伯格的这种态度,暴露了标准模型理论家的心虚:他们的理论其实是百无一用的。
一)李政道先生的开明
李政道教授在《场与粒子》一书中对粒子物理理论有一段比较开明的评论:“单是统一规范理论的标准模型就需要大约20个参数:e、G、θw、三代轻子及夸克的各种各样的质量以及四个弱衰变角θ1、θ2、θ3及δ。…… 因此,一方面,我们可能已经得到对于直到大约100GeV的物理过程的有效描述。另一方面,把我们已有的理论看成实质上是唯象理论更为合适。毕竟,谁曾听说过,一个基本的理论要求20个左右的参数呢?(李政道《场与粒子》,463页,山东科技出版社)
谁曾听说过?李政道教授自己当然听说过。粒子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应该都听说过。基本粒子标准模型要求20个左右的自由参数,在理论物理界早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李政道先生却说“谁曾听说过”,并不是他装着不知道,而是一种语言修辞,意思是“此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事情” ,“不可置信”。为什么一个需要20个自由参数的理论不可置信呢?请听听李政道的老师物理学先驱费米的说法:“如果给我四个自由参数, 我可以把任何实验数据拟合成一头大象。如果给我第五个自由参数,我可以让大象的鼻子来回摆动。”
五个自由参数就可以使大象的鼻子来回摆动,那20个自由参数可以有什么更神奇的法力呢?它们不仅可以拟合所有的实验数据,可以使大象的鼻子来回摆动,还可以使大象变种,变成鸟或鱼(粒子物理里面的行话叫做中微子震荡,夸克震荡或者混合,Cabibbo or CKM Mixing);它们可以精确地计算变种以后的大象有多少百分比已经变成了鸟或者鱼,将其表示成各种角度θw、θ1、θ2、θ3及δ的正弦函数;它们还可以让一只1盎司的蚂蚱生出一头5吨重的大象(质量为0.5 MeV的电子会衰变出质量为85 GeV的负W粒子和中微子),它们可以在“夸克禁闭”的名义下将各种无穷大抵消;它们可以禁止除上帝粒子以外的所有粒子具有质量,而必须通过上帝粒子获得质量。它们还可以从真空中无中生有地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暗物质暗能量。……总而言之,凡是20世纪理论物理里面的所有的天方夜谭和聊斋志异神话故事和超神话故事,都可以通过20个自由参数打扮成好像是高深严谨的数学物理理论。
凡是有一点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的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知道,一个需要20个自由拟合参数的理论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所以李政道先生才说“谁曾听说过”这样的理论呢?确实的,在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之前,没有人听说过一个正经的科学理论需要20个自由拟合参数。李政道教授对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这一批评,是非常致命的。因为,你不须要知道标准模型的理论细节,也不须要懂量子场论和粒子物理,你甚至根本就不须要知道物理,仅凭数理统计学的常识,就可以明白一个需要20个自由拟合参数的理论最多不过是一个数学游戏。李政道教授作为一个粒子物理学的权威泰斗,他的功名就是建立在对粒子物理的贡献上面。李教授对粒子物理标准模型能有如此深刻的批评,说明他的开明和诚实,令人肃然起敬。
二)李政道先生的谨慎
但是,李政道先生的开明是谨慎的,不彻底的。他只是指出了标准模型自由参数太多这一个致命问题,并没有深究与这些参数有关的假设和结论的荒唐和逻辑背理。比如e、G、θw、三代轻子及夸克的各种各样的质量以及四个弱衰变角θ1、θ2、θ3及δ等等决不仅仅是几个参数的问题,而是能够使大象变种,能够让1盎司的蚂蚱生出5吨重的大象,能够使夸克禁闭将各种无穷大抵消等等的非同寻常的假设和结论。李政道先生没有追究这些深层的根本问题的背理,只是轻描淡写地把全部问题归结为过多的自由参数(当然也是致命的问题),反映了李政道教授的谨慎:他现在还不愿意和标准模型决裂,还愿意跟着国际主流体制走下去。
我在“致中国物理学界建议书”中揭示了标准模型的一系列理论和逻辑上的根本问题:
1) 无穷大发散问题。 这包括二次量子化中零点能的无穷大发散,重整化问题和夸克禁闭等不同的表现形式。
2) 夸克禁闭和电荷量子化问题。
夸克必须带有分数电荷;根据夸克模型发展出来的量子色动力学(QCD)预言质子会衰变,可是预言的衰变寿命与实际观测的差好多个数量级。
3) 自发对称破缺机制。 规范对称性不允许任何粒子带有质量,这本身就说明规范协变性违背铁的物理事实。如果所有基本粒子的质量都需要通过上帝粒子来获得,那上帝粒子自己的质量从何而来呢?这岂不是数学化的创世纪?
4) 共振态问题。 将共振态认定为粒子,是一个基本错误,根本错误。粒子物理几十年的折腾,就是把这些根本就不是粒子的共振态当作粒子,为它们编排河图洛书,这才逼出了夸克模型。
5) 同位旋假定。 自核同位旋把质子和中子看成是同位旋空间的两个状态的概念开始,演变出了Cabibbo or CKM Mixing 等等玄学假定。这些玄学假定被一些自由拟合参数e、G、θw以及四个弱衰变角θ1、θ2、θ3等等包装成“数学”。
6) 太多的自由参数。 这就是李政道教授所说的谁都没有听说过的问题。
7) 弱电统一问题。 弱电统一标准模型只能处理电磁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同时存在的情形,可是却无法处理这两种相互作用单独存在的情形。这个理论还假定质量等于零的光子是由两个有质量的玻色子的组合,完全违背部分小于整体的科学逻辑,违背质量守恒定律。
8) 强相互作用理论预言与实验不符。量子色动力学 (QCD)预言的mu介子衰变和质子衰变的半衰期,和实验结果相差好多个数量级。
9)虚光子问题。 费曼图中的虚光子概念从量子电动力学一直推广到弱电统一标准模型,完全违背能量守恒定律。
所以,粒子物理理论的问题不仅仅是自由拟合参数太多的问题,更是因为与这些参数相关的大量基本假定和荒唐结论违反基本的科学逻辑和物理定律,也违背实验结果。所以,粒子物理理论的问题不仅仅是自由参数太多,更是假设太多,荒唐结果太多。可以说,粒子物理标准模型需要差不多20个基本假定(包括经典量子力学的几个基本假定,狭义相对论的几个基本假定,质能等价假定,二次量子化的几个假定,同位旋假定,重整化假定,将共振态认定为粒子的假定,规范协变性假定,夸克模型的几个假定,弱电统一理论中的假定,Crossing, Mixing,自动对称破缺假定,上帝粒子假定等等)来支撑的一座海市蜃楼。谁曾听说过,一个基本的理论需要建立在20个没有物理事实证明甚至直接违反物理事实或科学逻辑的基本假定之上呢?李政道教授,您听说过吗?
如果李政道教授不仅承认标准模型需要20个自由参数这样致命的问题,而且也承认标准模型的诸多假定和结论之荒唐,那他就实际上面临和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和主流的彻底决裂。可是李政道教授的开明是谨慎的。他不愿意和主流决裂,和既定路线决裂。这也是理论物理学界许多学术巨子的基本态度。
因此,李政道教授给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定性既不是“基本的物理理论”,也不是我所定性的“玄学理论”,而是比较模糊的“唯象理论”。
三)粒子物理标准模型是唯象理论还是玄学理论?
唯象理论是物理学中解释物理现象时,不用其内在原因,而是用概括试验事实而得到的物理规律。唯象理论是试验现象的概括和提炼,但仍无法用已有的科学理论体系作出解释。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唯象理论对物理现象有描述与预言功能,但没有解释功能。
让我们就用维基百科的这一定义考察一下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看看它够不够得上“唯象理论”的标准。
首先,粒子物理标准模型是“概括试验事实而得到的物理规律吗?”二次量子化将波函数认定为算符,有没有任何事实根据?重整化将无穷大认定为零,有没有事实根据?假定物理学上所有的动力学方程和拉格朗日函数都必须服从协变性,有没有事实根据?将散射截面能谱曲线上的共振峰认定为基本粒子,有没有试验根据?将违背能量守恒定律的虚粒子当作粒子相互作用中介,认定为普遍规律,有没有试验证据?将质子分成由带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电荷的夸克所组成,有没有试验根据?假定质量等于零的光子是由两个有质量的玻色子的组合,有没有试验根据?为了保证规范协变性而假定所有的粒子都不能带有质量,有没有试验根据?假定真空中存在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希格斯场,有没有试验根据?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几十年的高能物理试验,积累了那么多的试验数据,都是由粒子物理理论模型来解释的,这难道不能说粒子物理理论是“概括试验事实而得到的物理规律吗?”
不妨看看事实。在所有的衰变反应中,只要有强子的参与,理论就不能解释实验数据。于是理论家们就将核力分为强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将理论无法解释的那些试验结果剔除。即使经过如此筛选之后,弱电统一理论还是只能解释只有电磁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同时存在的一些散射数据,而不能处理任何一种作用单独存在时候的情形。这能说是“概括试验事实而得到的物理规律吗?”这种选择性的处理原则在上帝粒子的探测中已经变得非常荒唐。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不知花了多少亿美元探测上帝粒子,目的就是为了拯救标准模型。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正负电子对撞机(LEP)在1990年至2000年花了十年时间寻找上帝粒子,未能找到。美国费米实验室的 Tevatron 于 1995 年至2011年花了六年时间寻找上帝粒子,也没有找到。按道理,这些结果至少应该和LHC 2013年的结果具有同等的统计权重。可是粒子物理学界的规矩是,凡是否定的结果都被认为是失败,只有肯定的结果才被认为是成功,才有可能获诺贝尔奖。如果这次LHC寻找上帝粒子的结果是否定的, 同样会被认为是失败,直到得到肯定的或近似肯定的结果才肯罢休。这能说是“概括试验事实而得到的物理规律吗?”你们为什么不把欧洲核子研究中心1990年至2000在正负电子对撞机上寻找上帝粒子的试验结果,和美国费米实验室的 Tevatron 于 1995 年至2011年寻找上帝粒子的试验结果“概括”到粒子物理理论中去呢?
再来看粒子物理理论的预言功能。量子色动力学(QCD)预言mu介子衰变和质子衰变的半衰期,和实验结果相差好多个数量级。事实上,弱电统一模型不能处理弱相互作用或者电磁相互作用单独存在的情形,更说明了即使在没有强相互作用参与的情况下,其事后诸葛亮式的马后炮“预言”能力也是非常可怜的。
为什么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预言能力如此之差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不是真正“概括试验事实得到的物理规律”,而是从一大堆毫无试验事实根据的假定出发编织出来的玄学理论。用这个玄学理论去解释一些散射截面实验数据。把和实验数据基本相符的一部分算作成绩,把不相符的部分说成是另有机制(比如宇称不守恒,将核力分为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或者发明新的机制(比如Cabibbo and CKM mixing),或者引入新的内部纬度,新的量子数和选择定则,新的ad hoc measure 进行特殊处理。对于相差许多数量级的理论预言(比如mu介子衰变和质子衰变),就少提或者不提,在有人问及时就说“强相互作用理论还不太完备”。对于所有粒子都不能带有质量的荒唐结果,就提出新的假设如希格斯场和上帝粒子来“解释”,将本质上的不自恰变成“伟大的发现”,并吹嘘为到达天堂的“巴比通天塔”,“读懂了上帝的思想”,完全是神学星象学的做派。
为了对照,我们举一个天文学上有名的唯象理论作为比较。
在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被发现以前,泰提乌司(Titius)于1766年提出了一个计算六个行星半径的经验公式。其数学操作是这样的:1)他造出一个级数:
4,4+3×1, 4+3×2, 4+3×4, 4+3×8, 4+3×16, 4+3×32, 4+3×64, 4+3×128, 4+3×256……
得出如下一串数字:
4,7,10,16,28,52,100,196,388,772,……2)将上述数列各项除以10 得到各行星以日-地距离为天文单位的轨道半径数值:
0.4, 0.7, 1, 1.6, 2.8, 5.2, 10, 19.6, 38.8, 77.2, ……这些数字被称为“Bode-Titius numbers”,因为Titius的公式是被Bode首先发表的。这一规律被称为“Bode-Titius Rule”(鲍迪 — 泰提乌斯定则)。3)上述理论给出的轨道半径(第一行)和已知各行星的实际测量到的轨道半径(第二行)比较如下(以日 – 地距离为天文单位):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小行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
0.4 0.7 1 1.6 2.8 5.2 10 19.6 38.8 77.2
0.39 0.72 1 1.52 5.20 9.54 19.18 30.06 39.44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到,“Bode-Titius numbers”所给出的已知六个行星的轨道半径相当准确。对地球和木星轨道半径的计算和实验天文测量的数值完全吻合。这是非常惊人的成就。
当时小行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尚未被观察到。于是天文学家们开始按照“Bode-Titius numbers”来寻找,终于在理论预言的地方找到了小行星和天王星。这种惊人的预言力量使一些人认为存在一种什么力,决定着行星的轨道半径。
可是海王星和冥王星的位置却相差近三分之一和近一倍。这么大的误差是科学家无法接受的。
如果当时的天文学家们按照20世纪理论物理学家们的做派,就会大肆宣扬Bode-Titius 理论对地球和木星轨道半径的计算“误差等于零”,“超历史记录地好”;大肆宣扬这一伟大理论“准确地预算出了天王星和小行星带的位置”,“这种预言能力说明了Bode-Titius 理论是深层的理论”。至于海王星和冥王星的位置和理论预言的不符,则可以说因为他们离得比较远,可能是属于不同的相互作用。也可以引进一个什么额外维度和量子数以及相应的选择定则,将海王星和冥王星归入另一类行星。也可以在“Bode-Titius numbers”的基础上加上一个修正项,以得到所要的公式。这当然会使理论复杂一些,但是其复杂性和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复杂性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但是天文学家们没有这样做,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Bode-Titius Rule”(鲍迪定则)只不过是“唯象理论”而不是“物理理论”。为什么呢?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一,鲍迪定则是建立在一个生造出来的数列之上。这个数列没有任何物理机制为根据;第二,鲍迪定则预言的海王星和冥王星的位置明显不对,说明鲍迪定则只是一种有趣的数学巧合或者数学拟合,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或者放之太阳系而皆准的物理规律。虽然这种误差仍然在同一个数量级,但是对科学家们来说,30% 和100% 的误差已经是不可容忍的误差了。相比之下,20世纪理论物理中实验数据和理论预言相差30个数量级的例子已经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中文维基百科根据自己的定义居然把开普勒三定律和牛顿引力定律都认定为唯象理论,却是奇哉怪也。理由呢?难道是因为这些物理定律“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难道是因为“上帝的第一推动力”?如果连牛顿引力定律都要因为不能回答“第一推动力”的问题而算作是唯象理论,那我们真不知道科学上还有什么不是唯象理论。因为对任何理论我们都可以追问“为什么呢?”一直问到唯一的答案是“不知道”为止。
事实上,不但牛顿定律不是唯象理论,就是把开普勒定律算作唯象理论都会混淆视听。为什么呢?我们不妨把开普勒三定律和上面所述的鲍迪定则作一个比较。首先,开普勒定律不是从任何先验的假定开始,而是直接对行星位置的实验测量数据的数学归纳,而鲍迪定则是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级数出发,使其带有基本的玄学性质;其次,开普勒定律适用于所有的行星,彗星,以及一切围绕太阳运动的物体,其原理也适用于月亮绕地球的运动,以及别的恒星。总之,开普勒定律就是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在轨道学上的数学表示,和牛顿定律的适用范围是一样的。可是鲍迪定则除了六个行星的轨道半径以外,根本就没有普适性,因此鲍迪定则最多是一种颇有意思的记忆方法,一种唯象理论,而不是什么物理定律。
附3[转载] 苦心志,劳筋骨,翻过这坐山就是胜利
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是可以克服的困难。我们是在与世俗和偏见作斗争,而主流是在与大自然的法则作斗争。
主流现在掌握着几乎一切社会资源,所以很容易通过固有的社会科研机制和媒体得到公众的附和,得到大批追名逐利者的追随。这使得主流处处顺手,处处风光。但是他们的困难是如何向社会公众交代,他们花费大批纳税人的钱找到的暗物质在哪里?他们花费大批纳税人的钱找到的上帝粒子又在哪里?他们永远无法交代,为什么所谓“基础科学”永远无法对科学的任何部门产生任何作用。他们说要求基础科学对科学的其他分支产生作用是“功利主义”。他们要人们永远相信基础科学的全部意义就是维持一些理论家们的自我心理满足而不是推动科学的发展。这是多么巨大的不可克服的困难!
相反,致力于物理复兴的运动却有所进展。如果说,直到上世纪末,人们对理论物理的困境还不知情,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社会公众特别是科学界对理论物理的困境甚至荒谬就开始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了。而这,正是由于科学界还有我们这样一批追求真理的探索者的执著和启蒙。科学界虽然还不见得能够完全理解完全接受我们的全部观点和主张,但是许多人开始认识到对于宣称是基础科学的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和宇宙学标准模型还有一个真伪辨别和实践检验的问题;认识到对于这些玄妙的理论不能盲目追崇,而且还要考绩检验。
他们开始意识到,对一些所谓的前沿理论的考绩检验,不仅是一个学术自由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科学到底是沿着科学道路还是神学道路走的问题。新一代的物理学生们曾经以为学习理论物理的关键就是敢于抛弃不可动摇的经典理论去接受无法通过逻辑思维来理解的
不在理论物理学界的科学工作者以前可能以为粒子物理和宇宙学是离我们很远很深的东西。以为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不太懂,不能理解理论物理方面的所谓发现的意义,想来因为我们是外行,应该相信内行们的水平和诚实;现在他们知道不应该盲目地轻信;对于理论物理脱离科学其他分支却又耗费大量科研经费的现象,他们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只是看热闹,而会一年年地存心关注,看看这些热热闹闹的“理论突破”是不是和科学效用和社会需求的距离缩短了。如果这些所谓的理论突破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玄学故事,科学家们和整个社会对理论物理的玄学性质将会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也就是说,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现在花的银子越多,拖的时间越长,许诺的黄金时代越辉煌,对他们的压力就越大。这是主流所面临的困难的基本性质。这些,都与我们这些年来的启蒙工作分不开。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工作的成绩,不可气馁。我们的工作一定会潜移默化,孕育着科学的复兴。
当然,我们工作的困难,除了来自外部的打压,也有来自内部的困难。因为我们的主旨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难免众说纷纭,各执一端。
许多朋友都认为要挑战现存理论,必须有一个新的万能理论或者统一理论。这是完全不对的。大而言之,科学上不存在万能理论;小而言之,我们连什么是核相互作用都不清楚,如何统一所有的四大作用?追求大统一理论的想法本身就是天真的,也是主流理论物理的误区之一。我们内外挑战主流的探索者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受了主流思维的深刻影响,浪费了大量精力。
且不说科学以后还会发现我们现在想都想不到的相互作用,即使统一现在已知的万有引力,电磁力和核力,也要等到我们对核力有了清楚的了解之后才有可能。主流将核力分为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我们对核力并不了解。所以我劝朋友们不要在统一理论的追求上花费大量精力,更不应该期望甚至强求大家都接受自己的理论。如果大家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主流玄学的批判上,而不是纠缠在遴选某一新理论上面,也许共同点会多一些,不必要的争执会少一些。
有的朋友会问,如果没有一个比主流理论更好的理论,怎么能够批倒现存理论呢?能够的。因为现在行时的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和宇宙大爆炸理论,不是好坏问题,而是对错的问题。一个错误理论的谬误,不需要发明一个新的理论来证明,只需要从错误理论本身的逻辑背理和理论背理就可以证明。比如说,大爆炸理论的诸多逻辑矛盾本身就足以证明其谬误,不需要一个新的理论。
那么,DET理论不是新的理论吗?是的。但是DET不是一个统一理论或者万能理论。它只是解释宇宙红移现象的理论。它只是证明了,宇宙红移现象不能证明宇宙在膨胀。如果没有DET理论,能不能证明宇宙大爆炸是错误的呢?当然能够。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中的物质和能量全都是无中生有地被创造出来的,仅这一条就足够证明其谬误。同样,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不允许任何粒子,包括质子和电子,带有质量,而必须通过寿命仅有10的负22次方秒的“上帝粒子”获得质量。仅这一条就足以证明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谬误。其它如重整化,夸克禁闭,味道振荡等等概念,也都是违背科学逻辑的。
总而言之,对这种错误理论的批判,不应该以新理论的出现为前提。毋宁说,只有将这些错误的理论从统治地位上拉下来,理论物理才可能沿着科学的道路重新探索,才可能踏踏实实地从实验核物理开始实验数据的原始积累,新的正确的理论的产生才有可能。
您问到新作,我最近写了一篇“也来纠缠一下量子纠缠”,特附上。如您认为可用,可以登在您的博客上。
您也注意到我近来很少写中文文章了。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的主张和观点基本上已经发表在我的文集网站上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喋喋不休地重复这些意见。第二个原因是我终于看到了我不愿意接受的事实,那就是如果我不首先说服国际学术界理论物理已经走向了神学和玄学的深渊,要想中国学术界首先认识到理论物理的谬误是不可能的。
我的本意是希望中国能够首先跳出理论泥潭,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抢夺先机,将人力物理投在实验核物理和凝聚态物理上,在科学上引领国际潮流。我的想法可能过于天真。所以,现在我想我应该将精力主要集中在英文世界里。精神上我也找到了自我解脱。科学毕竟是全人类的事业,不能够因为民族主义的执著耽误了对整个物理学的历史责任。至于同胞们是不是理解并接受我的主张和呼吁,也只能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我的主张都在建议书中写着。如果同胞们觉得有道理,我任何时候都愿效驱驰。我准备把我的主张无保留地公诸国际物理学界。因为中西方文化和思维习惯的差异,英文版的行文风格也有些不一样。此后,我打算将我的物理复兴的主张在英文世界里陆续发表。要做的工作当然很多,真正有点“恐年岁之不吾与”了。
希望您和北相的朋友们保重身体。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成功。
王令隽
———————————————————————————–
也来纠缠一下量子纠缠
王令隽
最近有几位朋友同时送来一篇奥创智能网的报道,“50年物理难题盖棺定论,爱因斯坦被证明错了”,要我写点东西科普一下。这篇报道说,“爱因斯坦是量子理论的始作俑者,可他本人一生都不愿接受量子力学的怪诞结论。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上帝是不投骰子的”,旨在否定量子力学对物理世界概率性的描述。”“然而,几天前由荷兰物理学家发布的实验结果终于表明,爱因斯坦错了。”。这位荷兰物理学家(Ronald Hanson)做的是什么实验呢?是在相距1.28公里的两个实验室通过“量子纠缠 ”来超光速传播信息的实验。这篇报道一面说他的实验“无懈可击”,一面又说“两边的光子精确同时到达的成功率很低,大约1.5亿个光子对中才能有一对光子成功干涉并实现电子的远程纠缠。因此,该实验一共進行了22个多小时,却只得到245 次有效数据。不过,该团队目前正在努力改進,以期提高效率。”听起来好像有点底气不足,有懈可击。
我一直不太愿意去纠缠量子纠缠,除了分身乏术以外,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就通过实验得出结论的问题,根本不需要牵扯到深奥的理论和哲学。
量子纠缠最热门的两个研究方向都是实验课题:一个是量子计算机,一个就是上面这篇报道中所说的超光速信息传输,或曰量子隐形传输。前者纯粹从量子力学波函数的理论解释得到灵感,后者则是从激光物理实验中得到灵感。搞量子计算机的人们扬言,一旦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其威力将大大超过现有的数字计算机,能够破译数字计算机无法破译的密码,因此对军方有强大的诱惑力。军方也因此成了这一研究方向的重要资金来源。搞隐性传输的人们扬言,他们可以通过量子纠缠以超过光速很多倍的速度传递信息,并且保密程度非常高。国内有官方媒体甚至报道说遁术也是可以实现的。这些,当然也对军方有极大的诱惑力。不过,这两个研究方向扬言的前景都是可以实验验证的东西,而不是像大爆炸宇宙学家鼓吹的东西,是远在140亿年前或者几百亿年以后的故事或者现象,或者在谁都不能到达的高维空间,无法验证验错。研究量子纠缠的人们扬言他们的结果 – 量子计算机或者隐性传输 – 都是有直接的军事用途的,是可以用实验直接检验的。假如你是一个不懂量子力学的国防部总装备部的部长,可以问问他们,你们的量子计算机能不能破译这段密码?你们的隐性传输线能不能以超光速将这段情报加密发到西沙的边防站?这就是实践检验。
我曾经问过一位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从事量子计算机研究的朋友:你们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如何?比如说,你们的“量子计算机”能够做几位的加减乘除?和最简单的只能做四则运算的计算器(calculator)相比,性能如何?体积多大?价格相差多少?他不能答。近来好像不太听到有关量子计算机的报道。
相比之下,对量子隐性传输的媒体报道却风头正健,风光得多。这项研究其实也非常容易实验验证。电磁波以光速传播,已经不是什么尖端科学,而是被工程技术人员用于平常的作业之中的实用技术。举个例子,大型钢铁厂的电缆都是埋在地下的,因为走明线太危险。可是地下电缆也有问题。如果一条电缆因为过流而产生短路,就会烧断,工人们叫“放炮”。必须立即修复以恢复生产。可是因为电缆是埋在地下的,必须先找到事故点,才能挖下去维修。外线电工们有一种仪器,专门用来找事故点。方法是从电缆终端(通常在变电所)发送一个很尖的电脉冲。这个脉冲传到事故点以后就被反射回来,因此在示波器上可以观察到两个脉冲信号。这两个脉冲信号之间的时间差就是电磁波从电缆终端到事故点一个来回的时间。这个时间差的一半乘以光速,就是事故点离终端的距离。这个方法的精度大约在几米的数量级(否则挖土的工作量就太大了)。这种设备在几十年前就有了,应该可以用来比较测验量子纠缠隐性传输的速度到底是不是真的比光速还快。还有更直截了当的方法: 让量子纠缠隐性传输线和普通的电报线路同时在两个城市之间传送一段莫尔斯码,看看哪个先到达。根据上述这篇报道的宣传,“两个朝相反方向运动的光子,只要不受干扰,无论相距多远都可以在瞬间传递信息。打个比方,即使牛郎和织女分居在银河两头,彼此心映即刻完成,无需时间。”银河两头的距离是多远呢?大约30万光年。多宽?约1千光年。也就是说,一束光从银河这边走到那边需要一千年,或者说大约一千万小时。牛郎织女要在七月七日晚上相会,前后不到12个小时,时间很紧,见面以后还要执手相看泪眼,互诉离别之苦,问问小孩上幼儿园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还要留点时间做量子纠缠。这一切都要在王母娘娘早上睡醒横加干涉之前完成,所以他们飞过鹊桥的时间大概也就只有一个小时。即是说,他们过桥的速度应该比光速快一千万倍。可是量子纠缠专家们说“即使牛郎织女分居在银河两头,彼此心映即刻完成,无须时间”。就是说,牛郎织女量子纠缠的速度是无穷大!这是21世纪版的柏拉图恋爱!以这种速度和电磁波比,当然必胜无疑。
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量子隐形传输并不能传送任何物质或能量。量子隐形传态需要借助经典信道才能实现,因此并不能实现超光速通信。在量子隐形传输中,传输的只是“量子态”,而发送者和接收者都对这个量子态始终一无所知。这怎么能传送信息,应用于实际通讯呢?
能够传输“量子态”,却不能传输信息,这如何理解呢?举个简单例子。两个人打乒乓球,你只有两种状态:得分或者不得分。(这和电子相似,只有两个量子态:自旋向上或者向下。)你只要观察一个人是否得分,不用看另一个人(不用测量),就能知道他这球是否得分。又假如你有一对祖传的龙凤剑,也只有两个量子态:龙剑或者凤剑(又可叫做雌雄剑),母亲要你弟弟把其中一把从江南带到塞北你的戍边哨所。你打开一看,上面刻了一条金龙。你不用任何测量就立即知道妈妈留在身边的宝剑上刻的是凤凰,从你看到你的宝剑之时刻到你知道妈妈留下的宝剑是凤凰剑之间的时差,理论上可以等于零。如果用从杭州到雁门关的距离除以时间间隔,把结果定义为隐形传态的速度,它可以是无穷大。但是,这传递了任何信息吗?没有。真正的信息传递是通过经典传输手段,也就是你弟弟来传输的。他的速度取决于他是步行还是骑马。弟弟必须告诉你,另一把宝剑是存放在家里还是被妹妹作为嫁妆带到了岭南,也就是说,你必须知道游戏规则(理论)。在量子隐形传输实验中,规则(理论)是事先就知道的。这个例子所说的道理最早是由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Einstein, Podolsky and Rosen)三人提出的一个假想实验来说明的,叫EPR佯谬。
如果你有兄弟七八个,祖传有十八般兵器(多个量子态),那么当你看到弟弟带来的龙泉宝剑时,是不可能知道远戍辽阳的大哥收到的到底是杀手锏还是钩镰枪的,除非弟弟告诉你。另一方面,辽阳的大哥到底收到什么兵器,你无法改变,无法控制,因此无法传递信息。你要想传递信息,对方的某种物理量(比如对方耳膜的振动,无线电收发报机中的电信号)必须能够受你控制。而这些都是所谓的“量子隐形传态”做不到的。
不过,芸芸众生和国防部负责分配科研经费的首长们是不知道这个底细的。他们被 “量子纠缠的传输速度至少比光速高4个数量级。在量子纠缠的帮助下,带传输量子携带的量子信息可以被瞬间传递并被复制,因此就相当于科幻小说中描写的超时空传输” 的科幻宣传误导,以为他们的“量子纠缠”可以实现超光速信息传输,甚至还可以量子加密。如此神奇高超的技术,当然应该大力支持。国防科研要舍得花钱,哪里在乎几个亿?让他们搞去,以免外国人争了先机。所以“量子计算机”和“量子隐形传输”的科研经费源源不断。
朋友们可能会说,如果“量子隐形传输”并不能真正传输信息,却又要拼命宣传“量子纠缠的传输速度至少比光速高4个数量级。”“相当于科幻小说中描写的超时空传输”,那早晚是要被揭穿的呀?问题是,“早晚”是多长时间?社会心理对科研过程通常能够等待几十年。可是,几十年后,人们不就可以看出“量子隐形传输”到底能不能瞬间传递信息了? 如果你做不到,岂不是就真相大白了?社会心理的奥妙就在于此:几十年后,人们仍然会以新时间为起点,继续等待几十年,而不会质问说:“你们几十年前就说能够实现超光速通讯,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实现?”自上世纪末开始到现在,“量子纠缠”也热门了几十年了。时至今日,无论是量子计算机还是量子隐形传输,都还停留在研究室和新闻媒体,和实际应用毫无关系。但是人们不会计较这些,社会公众仍然会以今天为起点,再等几十年,好像以前几十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几十年后的公众,会以那时为起点,再等几十年。永远不会有考绩的时候。这里的关键之一,是要通过媒体向社会描绘诱人的未来和希望。如果某种研究某一天能够实现科幻小说中的
不管人们如何宣传公关,始终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从事量子纠缠研究的人们,一方面年复一年地宣称实现了多么伟大的“突破”,比如实现了八个粒子的纠缠态,另一方面又说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在理论探索阶段;一方面扬言量子隐形传态可以实现超光速密码传输,甚至可以进行远距离人体传输(遁术),可以不用宇宙飞船就把人送到其他的星球和其他银河系,另一方面又说量子隐形传态不可能用来传输信息和质量能量。这样既保鲜了美好的希望,取得了社会对现在的研究项目的资金支持,又对将来可能的失败有言在先,到时候可以推卸责任。
对量子纠缠的实际市场行情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以后,我们就可以来务务虚,谈谈理论与哲学问题了。玻尔曾说:“谁要是第一次听到量子理论时没有感到困惑,那他一定没听懂。” 其实,如果你第二次听到量子理论时没有感到困惑,你也还是没有听懂。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波函数”根本就不是行波的函数。光的波函数是经典电动力学中麦克斯韦场方程的解,非常简单的正弦波,而不是量子力学中任何方程的解。光波(行波,驻波)都是经典物理的概念。光波的传播,反射,折射,绕射,干涉,极化等都是经典物理光学的内容,和量子力学毫无关系。光的干涉现象和量子纠缠概念完全是不同的概念。量子力学中的量子态,是电子或其他粒子的状态,是薛定谔方程的解(且不管相对论量子力学)。可是薛定谔方程根本就不是波动方程,它的解根本就不是波函数,而是几率分布函数(正统教义如此说)。有的朋友说,行进中的电子也是波。我要他把电子的波函数写出来,他就是写不出来。至于描述电子的波动方程,就更不要谈了。教科书上总是举电子的干涉图案为例证明电子也是波。可就是教科书也写不出电子束的波函数。一写出来就会露马脚。如果不管有没有波动方程,只是偷用水波或者电磁波的行波函数,那振幅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呢?写不出电子的波动方程和行波的波函数,怎么可能实现“电子的远程纠缠”?尤其奇怪的是,电子的波函数怎么可以通过光波来纠缠?
不仅爱因斯坦不能接受“几率波”的不定论哲学,就是量子力学的发明者薛定谔也不理解。他提出了薛定谔方程以后,在求解方程时得出了量子化条件,算出了氢原子光谱的能级,结果和里得伯公式相符。但是这个方程的解到底是什么东西,薛定谔自己也不知道。好像只是一个空间的函数。反正得到了里得伯公式,解释了氢原子光谱,这就够了。
可是,对于薛定谔方程的解没有物理解释,就使整个理论蒙上了神秘的星相学色彩,使人感到非常不舒服,也给薛定谔方程的可信性甚至合法性蒙上了阴影。所以Max波恩就提出了一个解释,说薛定谔方程的解是波函数,其平方等于粒子出现在某一空间点的几率密度。按照这个解释,电子在任一时刻出现在空间的什么地方是不确定的。它既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那里。人们无法知道它的确切位置,只能算出它出现在某一空间点的几率。根据波恩的几率解释,说某个粒子某一时刻在什么空间位置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爱因斯坦在给他的回信中才说“上帝不掷骰子”,意思是物理世界的规律是决定的,物体或粒子在某时某刻的位置也是一定的,而不是随机的。
波恩是海森伯的老师,两人都是哥本哈根学派的重要人物。哥本哈根学派将量子力学的非决定论几率解释推向极端,居然认为一个系统的状态是不确定的,他的实现取决于观察者的观察或者测量行为。这个道理的一个直观例子就是,美洲印地安人到底存在与否,取决于哥伦布是否发现了新大陆。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印地安人是不存在的。薛定谔于是设计了一个假想实验,就是有名的薛定谔猫实验,来驳斥这种理论之荒谬。薛定谔猫实验是这样的:把一只猫封在一个密室里,密室里有一个密封的毒药瓶,上面有一个锤子,锤子由电子开关控制,电子开关由放射性原子控制。如果原子核衰变,则放出阿尔法粒子, 触动电子开关,锤子落下,砸碎毒药瓶,放出毒气将猫毒死。如果原子核不衰变,则猫就不会死。原子核的衰变是随机事件,也就是说,在一定时间内,猫到底是死是活是随机的。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哲学,在打开密室之前,这只猫处于一种死与活的叠加态。
薛定谔挖苦说:按照哥本哈根学派的解释,箱中之猫处于“死-活叠加态”,要等到打开箱子看猫一眼才决定其生死。(请注意!不是发现而是决定,仅仅看一眼就足以致命!)只有当你打开盒子的时候,叠加态突然结束,坍塌为某一本征态(叫做“波函数坍缩”)。但物理学中没有任何一个公式或者理论能够描述这种坍缩。尽管如此,长期以来物理学家们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还是接受了哥本哈根的诠释。但是薛定谔自己从来不接受这一解释。
哥本哈根派坚持:是的,当我们没有观察的时候,那只猫的确是既不死也不活的。他们有一句名言:“当我们不观察时,月亮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月亮本来是不存在的,当苏东坡观察到“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时,才突然坍塌出来了。等他和朋友“相与枕籍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时,月亮又坍塌到另一个状态了,不存在了。过了三个月,苏学士再游赤壁,又观察到“人影在地,仰见明月”,“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月亮又突然坍塌成“存在”的量子态了。苏老夫子返而登舟睡觉的时候,月亮又坍塌了,不存在了。可是此时说不定弟弟子由在另一个地方与睡梦中的哥哥“千里共婵娟”,于是月亮又不得不坍塌到子由的后院。这可不得把月亮忙坏了?问题是,在苏东坡看见“月出于东山之上”之前,“月亮本来是不存在的”。一个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如何坍塌出来呢?这岂不是无中生有的创造论吗?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观察到印地安人之前,印地安人是不存在的。同样,在此之前印地安人也从来没有观察到哥伦布和他的船队,因此哥伦布们也是不存在的。这样大家都不存在。如此类推,你很容易证明全人类和整个宇宙都不存在。这就是主张“当我们不观察时,月亮是不存在的”的哥本哈根哲学教给我们的深奥的哲学新思维。朋友们可能会说,王教授何必浪费这么多笔墨,跟这些没有常识的人较真?可是,就是这些非常荒唐的“你不测量,物理量就不存在”的教条,唐而皇之地充斥在量子力学教科书里,作为“新思维”(new paradigm)故弄玄虚,误导学生。当然,我实在不愿意浪费笔墨谈什么“人体传输”或“遁术”之类的东西。我不知道现在中国还有几个人相信遁术。
说到这里,我要谈一下爱因斯坦的物理哲学思想。大家都知道我对相对论是完全彻底地否定的。所以有的朋友以为我看到“50年物理难题盖棺论定,爱因斯坦被证明错了”之类的报道,一定会乐于附和,一起来反对爱因斯坦。恰恰相反,在对待量子力学和波函数的解释这个问题上,我是支持爱因斯坦的。他说“上帝不掷骰子”,说量子纠缠是“鬼魅般的超距作用(spooky action at distance)”, 反映了爱因斯坦的睿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比较复杂,很难简单地说成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他的思想中有相当的唯心主义成分,比如他把方程式形式上的美和对称性当作一种物理规律;把时间和空间当作数学变换参数而无视其物理本质;假定宇宙是有限的;假定现实世界是四维平直空间中的三维超球面;他毕生追求一个统一理论;等等。但是,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是有底线的。比如,他不能接受量子力学的不决定论;他相信,即使你不观察,月亮仍然存在;他主观上也尊重质能守恒定律,尊重因果关系(尽管他的相对论可能违反这些定律和关系);他认为宇宙是稳定的。当他发现自己的有限的三维超球面宇宙模型不能稳定时,便没有继续在宇宙学上折腾。他抛弃了自己提出的本质上是星相学性质的万有斥力宇宙项。他从来都不接受宇宙膨胀的理论,从来都不承认大爆炸宇宙学所依据的弗里得曼方程。所以,大爆炸宇宙学的许多荒唐结果与他无关。但是,他是相对论的创造者,宇宙项和三维超球面概念的始作俑者。宇宙学之所以坠入神学星相学的不归路,爱因斯坦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