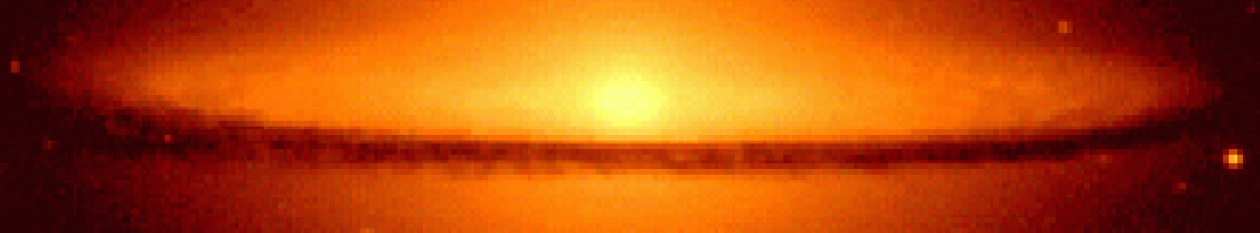科学的守护者:斯蒂文·温伯格(1933-2021)
斯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教授 | 图源wikimedia.org
撰文 | 施郁(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
责编|邸利会
本文近1万5000字,分7个小节,其中4、5、6节适合有一定物理基础的读者或专业研究者阅读。
“我们越反思生活的愉快,就越怀念曾经由宗教信仰提供的最大的安慰:对于死亡之后生命将继续的许诺,以及在来世中将与所爱的人相会。随着宗教信仰的弱化,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死亡之后,什么也没有。”
谢谢您。”
“现在的年轻一代物理学家也许嫉妒我们发展标准模型的激动和喜悦。这也许是个错误,正如我们这一代嫉妒量子电动力学的前辈英雄。我们新出道的实验家和理论家现在有机会参与迈出超越标准模型的下一大步。也许他们甚至能够看清通往显示终极理论的很高能量标度的道路。”
“所有好的科学家都依赖于直觉,以及关于什么是吸引人的理论的品味,从历史的意义上,他们感觉到领域在移动。这是很主观的。我们互相争论,这是社会过程。我和其他科学家有复杂的社会相互作用。这是值得社会学家研究的有魅力的现象。但是我认为,我们向一个客观真理汇聚,因为世界就是那样。最后,那成为稳定的、我们知识体系的永久部分。”
● 《量子场论(Quantum Theory of Fields)》(3卷)
● 《量子力学讲义(Lectures on Quantum Mechanics)》
● 《宇宙学(Cosmology)》
● 《解释世界:发现近代科学(To Explain the World:The Discovery of Modern Science)》
● 《近代物理基础(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s)》
《轻子的模型(A model of leptons)》的每年引用数
在此报告中,我将讨论理论物理中两条思路的发展。一条是我们对对称性的理解的缓慢增长,特别是在破缺或者隐藏的对称性方面。另一条是对于量子场论中无穷大的挣扎。在很大程度上,基本粒子相互作用的细节理论可以演绎地理解为对称原理和对付无穷大的可重整化原理的后果。我也将描述这些思路的汇聚如何导致我本人在弱和电磁相互作用的统一方面的工作。”
“我认为继续安静模式的实验物理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寻找质子衰变那样的稀有事例,因为我认为质子衰变甚至有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发现,我希望在深层地下的那种实验,人们可以耐心等待一大箱液体中的稀有事例。我希望那种实验也继续。”
“在宇宙加速膨胀发现之前,很多物理学家认为,有基本原理能够解释,为什么包括宇宙学常数在内的总的暗能量严格为零。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
“我所迷惑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表述量子力学的基本假设时,我们必须提到观察者,也就是,做测量的人。我希望在很基本的层次,我们有个非人格性的理论,正如艾萨克·牛顿的引力理论,我们从中可以推理出人的行为,但是人自己不出现在定律中。”
与温伯格教授在他的办公室合影 | 供图:施郁
“作为一位物理学家,回顾195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工作,那是非常大的乐趣。时不时发现一个理论想法,导致证实这个想法的实验,或者解释已知但是似乎奇怪的东西,这是多么令人激动。但并不总是这样愉快,很多时间花在了行不通的想法上。我经历的失败多于成功,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典型的。但是成功的少数情况弥补了其他的不成功。所以要坚持工作。”
[1] S. Weinberg, Lake View.
[2] S. Weinberg, Facing Up.
[3] R. P. Crease, C. C. Mann, Second Creation.
[4] S. Weinberg, Esssay: Half a Century of the Standard Model.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21, 220001 (2018).
[5] M. Hargittai, I. Hargittai, Candid Science.
[6] S. Weinberg, Nobel Lecture,Nobel Prize Website.
[7] Breakthrough Prize Website.
[8] S. Weinberg, Third Thought.
[9] S. Weinberg, Living with Infinities, arxiv:0903.0568.
[10] S. Weinberg, To Explain the World.
[11] 施郁,规范理论一百年, 知识分子,2019-03-31
[12] C. N. Yang and R. Mills, Phys. Rev. 96, 191 (1954).
[13] S. L. Glashow, Nucl. Phys. 22, 579 (1961).
[14] A. Salam and J. C. Ward, Phys. Lett. 13, 168 (1964).
[15] J. Bardeen, L. Cooper, and R. Schrieffer, Phys. Rev. 108, 1175 (1957).
[16] Y. Nambu, Phys. Rev. 117, 648 (1960).
[17] Y. Nambu, Phys. Rev. Lett. 4, 380 (1960).
[18] Y. Nambu and G. Jona-Lasinio, Phys. Rev. 122, 345 (1961).
[19] J. Goldstone, Nuovo Cimento 19, 154 (1961).
[20] J. Goldstone, A. Salam, and S. Weinberg, Phys. Rev. 127, 965 (1962).
[21] J. Schwinger, Phys. Rev. 125, 397 (1962).
[22] P.W. Anderson, Phys. Rev. 130, 439 (1963).
[23] F. Englert and R. Brout, Phys. Rev. Lett. 13, 321 (1964).
[24] P.W. Higgs, Phys. Lett. 12, 132 (1964).
[25] G. S. Guralnik, C. R. Hagen, and T.W. B. Kibble, Phys.Rev. Lett. 13, 585 (1964).
[26] F. Close, Infinity Puzzle.
[27] T.W. B. Kibble, Phys. Rev. 155, 1554 (1967).
[28] M. Baker and S. L. Glashow, Phys. Rev. 128, 2462 (1962).
[29] S. Weinberg, Phys. Rev. Lett. 19, 1264 (1967).
[30] A. Salam, in Elementary Particle Physics, edited by N.Svartholm (Nobel Symposium No. 8, Almqvist and Wiksell, Stockholm, 1968), p. 367
[31] S. Weinberg, arxiv:2101.04241.
[32] 施郁,物理学家温伯格首次面向中国公众的演讲,知识分子, 2020-11-02
[33] R. Newton, Am. J. Phys. 44,639 (1976).